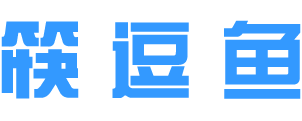作者:柳青壑
时隔二十载,华语流行乐坛再次迎来“刀郎年”。集创作、编曲、演唱、演奏、制作等角色于一身的音乐人刀郎又一次成为网络顶流,不仅给众多步入中年的歌迷带来一波“回忆杀”,也向我们提出了“刀郎现象”的命题。
华语乐坛的数据神话
2024年8月30日晚,刀郎在故乡四川资中举办《山歌响起的地方》线上演唱会。在没有炒作、没有预告的情况下,演唱会开播仅28分钟观看人数破千万,3.5小时的演唱会结束,在线观看人数5400万,直播间喝彩热度7.2亿,微信生态内曝光量达18亿,累计点赞量高达7亿,刷新了多项平台线上演唱会纪录。几天后,刀郎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单曲同样获得大量关注,他在成都、广州、南京、澳门开线下演唱会的计划同样让歌迷们激动不已。

刀郎举办《山歌响起的地方》线上演唱会。(图片源于网络)
2023年7月,以《聊斋》文本和民间音乐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山歌寥哉》发行后,充满讽刺意味的歌曲《罗刹海市》在短短几天之内引发了全网的讨论热潮。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罗刹海市”这个话题的相关视频就有58.1亿的播放量。《纽约时报》称刀郎“重回巅峰”①,《环球时报》刊文《刀郎新歌为什么成为一种现象?》②。
称其为“现象”是因为对歌曲的讨论已经远超音乐本身,而称“重回”则是为了突出刀郎沉寂许久、“归来仍是顶流”的号召力。因为刀郎早在二十年前成名之际就成为华语乐坛听众覆盖面最广的歌手之一,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行量超过270万张,这个数据在堪称“神仙打架”的2004年华语流行乐坛一骑绝尘。刀郎说“不想火,讨厌火”,但他还是屡次走进公众视野。
归来仍是舆论中心
世纪初的第一次走红后,刀郎面对的是对其音乐定位的雅俗之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质疑刀郎似乎有种强调自身审美品位的优越性以及维护流行音乐审美性的正义感,而近两年来对刀郎的讨论刚好相反,维护刀郎成为一种道德正义,批评则是站在了广大群众与客观现实的对立面。刀郎所面对的争论总是带有“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绝对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围绕刀郎音乐的讨论往往能映射出当今国人的审美趣味。
专辑《山歌寥哉》打破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编曲模式的刻板印象,将传统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材料、现实、根源、概念”解构并重组,建构了一套具有鲜明民族性的独特的流行音乐语言。
“山歌”是对冯梦龙《山歌》思想的继承,刀郎在《山歌寥哉》专辑封面中引用冯梦龙《叙山歌》:“书契以来,代有歌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说明对民间曲牌采集与运用的初衷。“寥哉”是蒲松龄的《聊斋》,既是歌词内容的依托,也是对山歌寂寥的感喟,而蒲松龄与冯梦龙都是不愿意在科举制度中“求同”之人。刀郎将历代文人通过保护民歌“藉以存真”的理想通过当代的“民歌”组成新的“山歌”,“以己之‘视界’,遥探他之‘视界’,合时代之烙痕”,其格局超越了他过往的所有专辑。
然而,其中的歌曲《罗刹海市》因讽刺意味浓厚、言辞犀利被过度解读,进而引发了一场全网的情绪宣泄。专辑本身也因此得到充分关注,各种网络平台上,各路学者争相从各种专业角度解读专辑甚至解读刀郎:文学界解读歌词中的“符号”与“所指”;哲学学者认为他经历了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精神历程;文艺学解释意向、文本,传播学解读歌曲走红利用的介质、媒介,甚至连专辑中的运镜也与音乐中某些深层含义相呼应;而流行音乐领域各音乐类型的博主从编曲、风格、演唱、演奏、传统性与创新性等多种角度盛赞刀郎。一部专辑照见众生相,与《聊斋》如出一辙。
对于刀郎演唱会的显著成绩,网络上出现大量的评论文章试图分析背后的“流量密码”,似乎刀郎的火爆主要来自幕后的精准操盘。虽然刀郎的音乐曾多次达到“顶流”位置,创造多种数据神话,但客观地说,刀郎的“走红”并不是因为针对网络用户的精准投放,刀郎音乐也不属于网络“快餐文化”,流行音乐中的商品性和娱乐性以及对大众性的盲从都是刀郎所抵触的。无论是2004年的销量神话还是近两年的现象级数据,在传播学的解释背后是刀郎作为音乐人厚积薄发的结果。
在以艺名“刀郎”走红以前,乐队出身的歌手罗林已经在音乐追求和试错的道路上走了多年。在新疆探索丝路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时期,罗林独立制作了《新疆原创第一击》《大漠情歌》《丝路乐韵》《丝路乐魂》《走进新疆之音乐篇》等音乐专辑,积极推动丝路音乐的发展,《西域情歌》翻唱的成功是对罗林在西域音乐风格长期探索和坚守的肯定。
而在2023年《山歌寥哉》引发全网舆论狂欢之前,刀郎在2020年10月推出《弹词话本》,11月用本名罗林推出以《金刚经》原文为歌词的专辑《如是我闻》,2021年推出个人专辑《世间的每个人》,甚至在2023年6月还曾推出个人音乐单曲《时光的信徒》。《山歌寥哉》并不是如媒体暗示的“二十年磨一剑”的“复仇之作”,而是他音乐道路上的一个脚步。
在刀郎的求索之路上,似乎总要被迫面对质疑声浪与“被质疑”的标签。在成名之初,新疆刀郎地区的当地人认为他“欺世盗名”,内娱主流音乐媒体认为他的音乐艺术性不高。然而在资中线上演唱会与成都的线下演唱会后,大众对刀郎的评价已从对刀郎风格的认同、人格的肯定拓宽到对刀郎音乐观的全面折服。当我们把目光从一切外在因素投向刀郎的音乐本身,会发现不是市场选择了刀郎,而是刀郎带动着大众音乐审美的转变。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具有“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征,是一种“社会的粘合剂”和“大众宣泄的工具”。刀郎最可贵的艺术品质在于正视内心真实的音乐观念,不“削足适履”迎合市场或主流文化的“标准”,这种音乐上的真实和个性使刀郎能够在公众视野中来去自如的同时,还能在音乐市场中顺利脱颖而出,并成为大众情怀的寄托。
文化的声音形式
在有据可考的争议中,对刀郎的主要质疑集中在“刀郎音乐是否具有音乐性”上,即在肯定刀郎歌曲的音乐的本质属性基础上的美学层面的探讨。在这一层面的对话中,原本的“主流”音乐界掌握着流行音乐的解释与批评的话语权,不仅从音乐审美与专业性上否定了刀郎,也从媒介受众的角度暗示刀郎音乐的欣赏者的社会属性。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尽管信仰神话可能失当,但嘲笑它则是一种误解”。从大众心理上来说,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还有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肯定:“对文化现象相同的理解可以给我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安全感”③。彼时站在流量之巅的刀郎,走到了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随即产生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之时,原本立足于形而上音乐本体论的音乐批评者们面对公然以商品为本质属性的音乐类型毫无招架之力,不待乐坛做出反应,大众的音乐审美价值已被迅速重构,内地流行音乐市场产生了新的“主流”,不得不正视新的市场格局。
因此,刀郎是流行音乐文化在媒介化发展过程中的典型。“音乐与媒介融合沿着摧毁传统音乐形式、重构新的审美价值的路径同时展开,是从形式到内容‘破’与‘立’的共时性过程。”④在刀郎线上音乐会成功撬动市场后,行业重新认识了不同群体的流量转化以及这种产业融合带来的新的发展空间。对刀郎的争议是流行音乐产业格局变迁、媒介转型时期产生的矛盾的集中投射,而刀郎的走红除了音乐方面成功,也是顺应媒介文化发展趋势的结果。
至于刀郎的音乐是否有音乐性?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还会持续发酵,流行文化本身就是历时与共时的。但刀郎在成名初期直白、通俗的音乐与2024年刀郎在资中线上演唱会上展现出的如同“整体艺术观”般的音乐素养有很大差异。他在演唱会的开场中坦白:“从最早开始的感官式的与世界交互所投射的内心的冲动与宣泄,到后来理念式的由内心向外寻找空间和时间的思考……以此来探索边界,寻求自由。”这似乎解释了刀郎二十年间音乐风格的变化。
一个音乐人的作品被广泛认可,不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是无瑕的、不能被讨论的。在古典音乐领域,人们对于作曲家不同时期风格的转变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每一时期每种风格的作品都能奠定作曲家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刀郎在《2002》时期的音乐是直截了当的“冲动与宣泄”,其音乐特征在于刀郎嘹亮沧桑的声音和西域音乐风格上的辨识度;而从《弹词话本》开始,专辑的艺术性、思想性、文学性都有了质的飞跃,甚至为理念式的探索建构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新的流行音乐语言体系。我们没有必要以《山歌寥哉》的思想深度对“西域情歌”时期的直抒胸臆进行辩护,这两种音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刀郎。即使在相同创作时期,刀郎《冲动的惩罚》在2007年于北京召开的“抵制恶俗网络歌曲”座谈会上被中国音协40多位知名音乐家点名批评,歌曲《一家人》和《爱是你我》却分获第11、12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刀郎歌迷对刀郎歌曲遭受的负面评价充满焦虑,宁愿以阶层对立自洽也不愿意正视自身喜爱“俗乐”的可能性。而刀郎本人却在归隐市井多年后,用《弹词话本》和《山歌寥哉》两张高品质的主题概念专辑正面展示了民间音乐从古至今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让批评者们重新思考“俗乐”的定义。
恰当的音乐批评是对音乐的反思和监督。“只有深入挖掘音乐背后的符号逻辑,才能理解流行音乐的本质,也才能通过传播来反哺、修正内容的生产”⑤。流行音乐领域的音乐批评应该鼓励音乐层面更多元的选择、更理性的思考,为音乐之“辨”而“辩”,在良性思想碰撞平台上将不同观点转化为对流行音乐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不是某一绝对审美标准的堡垒。
在这一过程中,刀郎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他在“标准”之争意外选择了“探索边界、追求自由”,回到音乐理想的初心“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唱“山歌”重回顶流的刀郎身体力行证实了流行音乐大众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是可以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这种不盲从、不妥协与不放弃的态度让资本笼罩的流行歌坛的从业者们重拾对艺术理念的坚持,也让大众重拾对流行音乐艺术性和民族性的信心。
琵琶演奏家吴蛮曾说,世界音乐节上的中国声音太少了。刀郎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流行音乐的声音吗?在刚刚结束的成都演唱会上,刀郎演唱了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川江号子》,短视频推出后又迅速火遍全网。四川听众对此热血沸腾,认为刀郎的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演唱会的意义,唱出了川渝人的精神力量。刀郎为流行音乐开辟的“山歌”体系,使他成为区别于音乐学家与作曲家的另一种“拾遗者”,让濒临成为“文化遗产”的民间音乐与高居庙堂的传统音乐重新走进更广阔的公众视野、焕发新的生机,这种选择本身已经将大众对文化认同的期待转向对文化自信的认识,进而产生更深刻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音乐视野面前,关于审美标准的讨论已经黯然失色了。
当下刀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然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是当代华语乐坛与未来的流行音乐史都无法忽视的存在。在推波助澜的评论浪潮中,如果不能冷静地分析“刀郎现象”、客观地评价刀郎音乐,那今日的盛赞也可能成为捧杀,同昨日的质疑一样让我们错失又一次对“刀郎热”现象反思的机会。
刀郎说希望他的所有创作能够成为“‘见而不识、识而不义’的探索未知的过程”,而不是“传达某种特定思想观念和美学理想的载体”,更像是无形的“大象”。因此,对刀郎议题的解释和意义也许正是当代流行音乐批评、音乐传播以及音乐社会学的重要切入点。华语乐坛终将必须正视刀郎现象的相关问题,而不是争论个体的能力、态度与具体的音乐指涉。
【注释】①Amy Qin,“Dao Lang, China’s Pop Star, Returns to the Top”,New York Times,7/26/2023.
②Why has Dao Lang’s latest song become a phenomenon?Globle Times,Jul 31,2023
③刘小波.符号互动与泛符号化: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2022年第8期.
④刘强,李慧.论音乐媒介化与审美价值的重构[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⑤刘小波.符号互动与泛符号化: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2022年第8期.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艺评空间